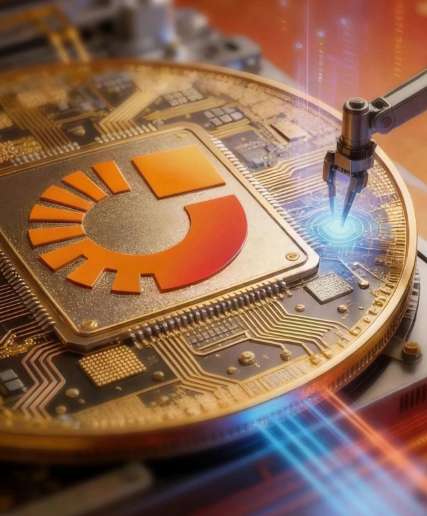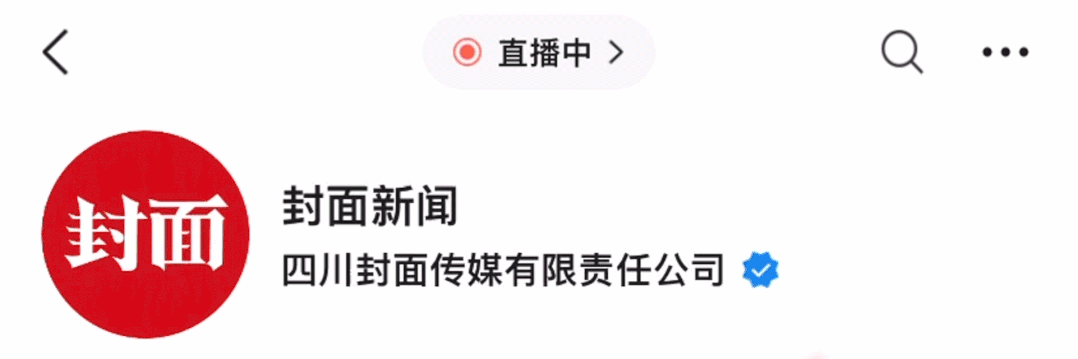AI时代的工具崇拜:效率至上与新型社会等级

在全球范围内,人工智能(AI)正迅速成为一种新的共识:人人都应该学会使用AI。掌握AI的人被视为“跟得上时代”,而不会使用AI的人则隐隐被视为“迟早要被淘汰”。这种观点在媒体上广泛传播,诸如“一个人顶一支团队”的口号层出不穷。这种叙事将复杂的社会劳动简化为单纯的算力输出,试图构建一种“效率至上”的技术乌托邦。
表面上,这是一场工具革命,实际上更像是一场价值重排:谁先进、谁落后;谁高效、谁低效;谁值得被投资、谁可以被牺牲。技术焦虑因此并不只是一种“学习焦虑”,它更像一种身份焦虑——你担心的不是“我会不会用”,而是“我会不会被归类”。
技术焦虑与社会等级
要理解这种焦虑,必须先承认一件事:技术从来都不只是一套方法,它总会携带一种社会性的评价体系。所谓“效率”“进步”“创新”,在不同语境中常常并不是中性的词,而是可以用来划分等级、制造边界、分配尊严的词。人们以为自己只是在讨论工具,实际上是在讨论谁更体面、谁更可被替换。
在《镀金的鸟笼》中,这种逻辑被描述得尤为深刻。当一个社会高度强调工具理性时,技术转型往往伴随着对“过去”的道德审判。所谓“高科技”“高精尖”不仅是产业分类,更是道德等级。那些曾经解决大量就业、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业,却在转型叙事里被称作“低端”“污染”“重资产”。
“倒闭、破产、下岗、辞退不再被理解为结构性变化中的代价,而更像一种‘你活该’:活该你不够先进,活该你被时代抛下。”
AI在职场中的新标准
今天围绕AI的热潮,正在复制类似的机制。AI当然能提升效率,但当它被奉为圭臬,效率就会从“手段”变成“道德”:快是对的,慢是错的;自动化是对的,手工是落后的;会用AI是体面,不会用AI是“你该努力”。于是“工具”变成了“标准”,“标准”变成了“筛选”。
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说,互联网越来越机械,设计部门、视频部门甚至被要求把“使用AI辅助创作”写进KPI。于是AI不再是“你觉得好用就用”的工具,而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指标。我们进入了一种“为了科技而科技”的状态:不是因为它真的让作品更好,而是因为“不用AI”会显得落后。
“当组织把大量精力花在证明自己‘在工作’、完成可展示的指标与流程,而不是在创造真正有意义的成果时,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机械。”
AI与新型剥削手段
更进一步说,当AI不只是“可选工具”,而是被写进流程、写进KPI、写进绩效考核时,它就可能变成一种新型剥削手段:同样的工资,要求更高的产出;同样的工时,塞进更多任务。在“效率提升”的名义下,把原本应该由组织承担的成本——学习成本、适配成本、加速带来的焦虑与风险——转嫁给个人。
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里提醒我们:当“更快、更强、更能产出”被内化为一种道德命令时,剥削就不再主要来自外部强迫,而会变成一种自我驱动式的过度消耗。你把自己当成项目来优化,也把自己当成机器来催促。
“你必须更快交付、更频繁迭代、随时在线优化,甚至还要为机器生成的瑕疵背锅。”
结语:重新定义人的价值
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,我并不是要否定AI的价值,也不是反对技术进步本身。AI在很多具体情境里确实能节省时间、降低门槛、让更多人获得原本难以触及的能力。问题不在于工具,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工具,以及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人。
当对技术的掌握被默认为一种“优越”,当对效率的追求被当作道德与体面的标准,技术就不再只是帮助人,它开始参与划分等级。我的反对,指向的正是这种把“会不会用AI”“够不够快”当成价值评判尺度的社会气候。
“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‘AI会不会取代我’,而是:当AI变成一种道德标准,我们会不会把许多本来正当的劳动、正当的缓慢、正当的非标准,一起打包成‘落后’。”
如果我们把“不会用AI”当作一种缺陷,把“手工”和“慢”当作一种可笑,那么被淘汰的不只是技能,更是一种对人的理解。人不是乘法关系里的某个环节,不该因为某项工具的熟练度就被归类为“零分”。
一旦“效率—体面—价值”的链条被固定下来,“低端”就会不再是某个行业或岗位的描述,而会变成一种可扩散的羞耻机制:它可以落到任何人身上——落到没有时间学习的人身上,落到需要慢工出细活的人身上,落到更重视关系、照护、情感劳动的人身上,落到所有无法把自己变成“可量化、可比较、可替换”的人身上。